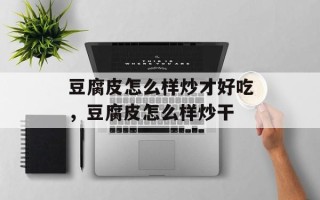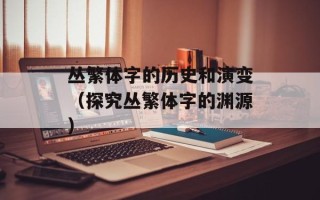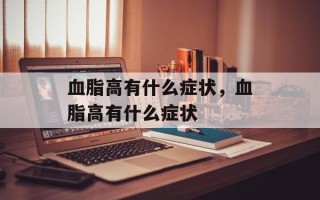今宵明月最圆光
睦睦全家聚一堂
馋嘴娃娃吃月饼
爸爸对月想文章
文化考释: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与春节、端午并列的三大节日之一。过去成都民间一般把过春节叫作“过年”,把端午叫作“端阳”,把中秋叫作“八月十五”。
成都地区过中秋的习俗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全家团聚、饮酒吃肉、拜月亮、吃月饼是最普遍的习俗,有的地方也有放河灯、放孔明灯的。
今天市场上的月饼琳琅满目,品种众多,过去成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今天最常见的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都是 *** 战争时期才传入四川的, *** *** 以后才大量增多。过去在成都地区最常见的月饼样式是麻饼,主要有红糖月饼和白糖月饼两种。笔者幼时特别喜欢红糖月饼,把它放在微火上慢烤(例如放在灶膛中),粘满芝麻的皮壳会变得酥脆,里面以红糖为主料的馅会流淌出来,特别香。
虽然过去的月饼品种不多,但是民间过中秋时还有一类食品必不可少,就是这时几乎全都同时成熟的各种水果:梨、石榴、柑子、橘子、枣子……由于水果很多,在成都地区还流行一种与水果有关的游戏,就是在中秋夜里耍流星香球:先将柚子(过去叫“气柑”)用绳子编网套上,系上绳子,再在柚子上面 *** 上几根点燃的香,就可以手持绳子沿街舞动,几根香火有如几颗流星,十分好看。清人冯家吉在《锦城竹枝词百咏》中写道:“茶半温时酒半酣,家人夜饮作清谈。儿童月饼才分享,又 *** 香球舞气柑。”
过去在中秋之夜可以到旁人家的菜地中去摘菜,叫作“偷青”,菜地主人不会责怪,反而认为是一种吉利。特别是摘下大南瓜送给求子人家,更是十分热闹的喜事。民间有这样的四言八句:“八月十五送南瓜,满堂香火放光华。观音菩萨多保佑,来年生个胖娃娃。”
作者:绘画 杨麟翼 竹枝词 江功举
文化考释:袁庭栋
《蜀中风俗图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 *** ,报料 *** :338 *** 05712】
要问正月初九的庆阳哪里最热闹?宁县院子上九庙会看过来何为上九?早胜人最在行。宁县早胜院子村有个玉皇庙,初九唱大戏,拜求玉皇,风调雨顺、万事亨通,故早胜塬上的人赶庙会,称之为赶上九庙会。
庙前香火正隆
庙会起源于寺庙周围,所以叫“庙”;又由于小商小贩们看到烧香拜佛者多,在庙外摆起各式小摊赚钱,渐渐地成为定期活动,所以叫“会”。久而久之,“庙会”演变成了如今人们节日期间,特别是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
对于生活在陇东早胜塬上的千家万户,上九庙会,可谓是馋嘴娃娃的世界,也是爱耍碎娃的天堂,更是古稀老汉老妪的戏曲盛会。
海盗船进"村"了
爱耍碎娃的世界
原味小吃再显庙会
热闹的大戏唱起来
这才是最惬意的风景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是中 *** 间 *** 及岁时风俗,一般在农历新年、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节日举行。也是中国集市贸易形式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和地庙的 *** 活动有关,在寺庙的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多设在庙内及其附近,进行祭神、娱乐和购物等活动。庙会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
而正月初九正会这天,更大的热闹还是这些群众喜闻乐见、自发组织的闹社火,踩高跷、三打白骨精、红脸耍大刀的关公。
社火团队走起来
喜庆的秧歌扭起来
演出队的纪念合影
社火彩车走起来
看我红脸的关公唱首道尔顿
在中国西北,每年春节,各乡村群众自发组织各种社火活动。社火规模从几十人到上百人,包括锣鼓手,舞狮等等。群众燃放爆竹迎接社火队伍,并赠予烟酒等礼物。社火经过之处,爆竹声声,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气氛热烈。
要问正月初九庆阳的哪里最热闹?还是院子上九庙会走一遭的好!
图/清华丹青)
源自:陇原风语
*** 反复作乱,当家里储备的粮食逐渐减少时,心中不免有些不太淡定了。如果长此下去,不得不考虑由吃饱喝足到七成饱,从七成饱到半成饱的节食计划。这不禁让我想起老家常说的一句话来——有了一顿,没了挈棍。
这句话在我们老家主要是说给两类人听的。一类是馋嘴的娃娃,一类是好吃懒做的浪子。
上个世纪70-80年代,我们老家还很贫穷,虽然说不至于食不果腹,却总不能饱食。尤其是像白面这样的精细粮食更是无法奢望。所以,乡邻们经常把能吃上白面作为鼓励孩子刻苦读书,进而为官的“诱饵”。即便如此,作为父母,也总会想方设法或变着法儿的改善生活。比如说煮洋芋吃得多了,便把洋芋擦成丝,靠着淀粉的黏 *** 烙成洋芋饼;玉米面疙瘩吃久了,便将玉米面发起来,盛入碗中,再倒出来蒸成一种碗状的厚馒头,叫作“玉米面碗簸子”。概言之,就是把猫叫成 *** 。可就是这样的一些改变,都会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尤其是娃娃们,每次在烙洋芋饼或做“玉米面碗簸子”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守候在锅巷里。“美味的食物”出锅后,就顾不得烫手烫嘴,狼吞虎咽地吃将起来。甚至等不到下地干活的家人们回来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每当此时,主厨的母亲总是又气又疼。责怪孩子说:“有了一顿,没了挈棍。”也就是说,有好吃的,便毫无节制,短时间吃完,就不知道省着点吃,更不考虑要吃得久些。
我小时候,确实见过借粮、借面、借油、借盐之事,但主要是家中来了尊贵的客人,却没有像样的吃喝来招待,便向好过家讨借一升白面或一碗清油。否则,即就是吃糠咽菜,只要不饿肚子,也绝不会向他人张口。可是,当时的农村,还有一些成年人,过光阴毫无计划,以至于田地荒芜,颗粒欠收。到头来缺吃少穿,日子过得很是惶惶。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揭不开锅时,便求助于人。总会有好心人救助与他。借给一袋粮食,或争取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但得到救济的他,也像小孩子一样,撑爆了肚皮的吃喝。没过几天,救济粮吃完了,救济款花光了。喝风阿屁的日子再一次来临,只好等着明年这个时候的救助了。面对这种“寒号鸟”式的人,读书人立 *** 想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句话来。而村民们则说他是“有了一顿,没了挈棍。”也就是说,有吃有喝有钱时,一次 *** 吃完用完,等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挈棍”。
“挈棍”的“挈”,我们读作qi?,应该是取拿、携带之意。而“挈棍”,便是拿着木棍或棍棒的意思了。那么,“挈棍”为何呢?这里不妨先说说秦腔《八件衣》中的叫花子仁义。他曾向世人夸耀说养活他的有三件宝——铺盖、木棍、筷子碗。碗筷一日供三餐,睡觉全靠铺盖卷,而木棍的主要用途就是打狗。因为,行乞之人走街串巷,经常会遇到狗咬,所以,一根木棍便是 *** 的 *** 。在《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把一根木棍给了苏三,说“给你一根棍儿,权当三条腿儿,走路多得劲儿”。可见,对于乞讨的人来讲,腹中饥肠辘辘,还要持续行走,这一条棍儿,可不就是一条“腿”吗?这样一说,读者就很清楚“挈棍”的意思了。
老家的有些话,的确是充满哲理的。就比如“挈棍”这两个字,很形象, *** *** 的。小时候,虽然朦胧之中也知道它等同于要饭,但毕竟不会想得太多。现在回想起来,这“挈棍”二字,其实不单单指代讨饭,而是有着更多层次的内涵和用意。在我看来,首先,“挈棍”是一句警示之语。用来告诫那些好吃懒做之人,如果不肯付出,只盯着上一顿,不考虑下一顿,则离“挈棍”乞讨的日子不远了;其次,“挈棍”是一句劝学之语。用来劝告那些读书之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想不“挈棍”,只有苦用功;再次,“挈棍”是一句劝耕之语。民以食为天,农以耕为本。如果不能读书把功名取,则应该好好务农。如果作为农人,而懒得耕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话,便只好“挈棍”讨吃了。
“有了一顿,没了挈棍”。告诉我们凡事要未雨绸缪,要有忧患意识,要勤俭节约,莫可只顾眼前,莫可铺张浪费,否则可就真要流落街头,寻吃讨喝了!
文:白吉祥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昔日的老屋,曾经欢歌笑语,炊烟袅袅升起;三十多年后再回首,看不到熟悉的背影,看不到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野草丛生,破旧凄凉,只留下美好的记忆和牵肠挂肚的思念。
老屋是就地取材砂石砌成的窑洞,看上去工艺粗糙、千苍百孔但非常结实,冬暖夏凉是几代人安居的幸福乐园,倍感无比温馨。
在我记事时,老屋是并列着的三间窑洞,属于我家的只有两间。一间算是一大家人居住的“卧室” ,另一间像似“博物馆”陈放着爷爷遗留下来的一些瓷盆破罐,生活用具。几口黑灰色瓷瓮整齐地排列成一排在地下摆放着,里面只能放些碎米碎面的;老屋的正南有几间属于集体的瓦房,看上去年代久远破烂不堪,后被农业社拆除 *** ;西南一角是我家磨面的磨房。听妈妈说,在老爷爷手上仅有一间窑洞,还是土改时 *** 分给的,后来爷爷咬紧牙关又在别人手里买下了隔壁的另一间。
传说中的老屋原来是一户富裕人家的四合头大院。院里油酒醋坊、粉坊豆腐坊和皮毛加工样样齐全,生意做的很大,远销内蒙、太原等地。酿造的白酒,口感香淳气味浓烈,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其名远扬。长工短工已有数十多人, *** 满圈,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人家。老屋正北面精雕细刻的花儿大正房在 *** 时被 *** 一火化为灰烬。新 *** 来了所剩家产全部归公,三间窑洞在土改时期分给了村子里的穷苦人。老屋何年建造?已无法考证。
老屋,坐落在村子的中心地段,出入方便,视野开阔,抬头可望十里八里之外。清晨,太阳露出半个笑脸,窗户上像撒下一片金光,照的满窑洞通明,屋里暖烘烘的。宽敞的院子,已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地方。村里放 *** 、唱戏都在这里进行。炎热的夏天,午后屋檐下乘凉的男女老少 *** 在一起,说东道西啦起家常,议国事、说笑话,你一言他一语,笑声不断。男人们“吧嗒吧嗒”不停地 *** 旱烟锅,一锅接一锅,丝丝青烟悠悠飘然散发出呛人的烟丝味。娃娃们坐立不安,你追我赶瞒院子撒欢。直到队长发起下地劳动号令,人们才陆续走开。
妈妈总是每天睡的很晚很晚,从来不把今晚做的营生推到明天。老屋那盏昏暗的油灯是我们和妈妈最忠实的伴侣,写完作业等妈妈检查后,还要和弟弟在油灯下开心一会才晚睡。有时我一觉醒来看到妈妈还在灯下缝补。到了年关,妈 *** 眼睛都红肿了。
黄土高原上的冬季时常刮着刺骨的西北风,冷的人直打哆嗦。故乡的积雪有时厚的没过膝盖,雪过天晴太阳刺的让人睁不开眼。屋顶上积雪融化的雪水凝结成一个个晶莹透亮的冰棒棒挂在屋檐下, *** 着馋嘴的娃娃们。这时,我就寻找父母不在家的机会,偷偷地吆喝几个伙伴小心翼翼地瞄准冰棒棒用木杆猛击,然后把击落的冰棒棒用衣袖裹起来,咬一块清脆爽口,就像城里的孩子们吃冰棍甜到心底。这时,小伙伴们一个个脸蛋上露出惬意的笑容,一溜烟跑的无影无踪。
那年代,也许是穿不暖,也许是天气特别寒冷,常常冻得直跺双脚,两只手缩在袖口里半天不敢伸出,只要回家坐在妈妈烧暖的炕头上,寒冷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每年冬季农闲时, *** 总要约定几个“窑黑子”冒着生命危险钻到几百米深的煤窑里掏碳,用它换些米面贴补穷生活。每天鸡“喔喔”一叫, *** 摸着漆黑,冒着严寒手握冰冷的铁镐就下窑了。中午只吃些窝头、炒面等干粮,等到回家时太阳快落山了,浑身黑的像个“非洲人”只能看到几颗雪白的牙齿。白天,小煤场就像赶骡马集,人欢马叫热闹至极。为了抵御漫长严寒的冬季,附近村子赶着 *** 驮碳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多数是拿些米面来兑换煤炭取暖做饭。出窑的煤碳你挣我抢吼叫成一片,生怕自己空手回家。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常来凑凑热闹,然后才回家。
直到进入腊月,农历的十一月三十日这天,煤场又是放鞭炮,又是摆贡品热闹一番 *** 才正式上窑收工。
小煤窑,不知祖祖辈辈延续了多少年,又不知救过多少人的命。它是故乡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也吹醒了故乡那片沉睡的土地。束邦的手脚终于解开了,人人迈出坚定的步伐,甩开膀子大干。父母也使出浑身解数,不断拓展作物种植面积,沟沟洼洼、地头地尾也要点瓜种豆。披星戴月辛勤地耕作在那几十亩地里,双手磨出了厚厚的死茧,带血的裂缝疼痛难忍,日子总算有所改变 。一年下来,隔壁属于集体多年的另一间窑通过正式交易属于我家所有。紧接着,父母决定在老屋右侧的空地上再新建一间。
第二年春季,在众多乡亲的帮助下,崭新的窑洞终于落地而成。又是泥墙、又是粉刷装修的亮堂堂,感觉无 *** 温馨全家人心里乐呵呵的。
从此,一个完整的院落属于自家所有,终于圆了父母多年来的夙愿。
西南角的磨坊,也改制成了牛棚和放草料、耕犁锄头等农用工具的“杂货店”。
后来,妈妈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杏子树。春天,粉红色的杏花香随风飘散,淡淡的清香令人陶醉;秋天,绿叶里裹着黄橙橙的杏子那么 *** 喜爱,整个院子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十分优雅。
这,就是老屋!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逐步长大,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看到老屋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老屋见证了我们兄弟姐妹们的成长,见证了历史。详实记录了我们童年时期最青涩的那一部分。老屋是情,老屋是根,老屋更是一种精神文化。老屋给了我们心灵归宿,老屋给了我们真正的宁静和安详,老屋传承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食量。我们全家人住在老屋,心酸苦楚在老屋,欢歌笑语在老屋,永不磨灭的记忆仍然在老屋。
遗憾的是,老屋在近年 *** *** 的大朝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幸好在那年的清明节回到故乡拍下了这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那次,竟是和老屋最后的告别。
故乡的老屋已不在有,老屋的灵魂还在伴随着我们,老屋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我思念故乡,思念故乡的老屋,思念远去的亲人。
本文 *** 来源于 *** ,若侵权联系删除。欢迎文友原创作品投稿,投稿邮箱609618366@qq *** ,本号收录乡土、乡情、乡愁类稿件。随稿请附作者名,带 *** 更好,请标注是否原创。乡土文学公众号已开通,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xiangchouwenxue,关注我们。
“横”菜【中国故事】
作者:方言(中国作协会员,现居北京房山)
有一道“横”菜,已在我家餐桌上驰骋多年。闺女和侄女年幼,从味道认知,叫它“香肉肉”; *** 则叫它“蒸碗儿”;媳妇沿用娘家的叫法“扣肉”;母亲忆苦思甜,从前日子过得紧巴,庄稼主儿哪儿吃得起?现在日子好了,奔上了小康,应该叫“好日子”!我说这道菜咱家人人爱吃,叫“吃不腻”更贴切。弟弟从小嗜肉如命,眼 *** 重触了红线,天天嚷着要减肥,可一看见这红亮的大肉片,就认“栽”了,无奈地说:这盘菜最应该叫“绊脚石”。全家人都被他逗笑了……
“横”(音hèng)菜,京西方言,指烹饪做法繁复的纯肉食菜肴。 *** 亲精于厨艺,最拿手的“横”菜有两道,“好日子”为其一,另一道叫“血脖二刀”。
血脖二刀,是人间的一道美味。不过她也有很多年不做了,原因是食材很难找到。
我小时候,村里还有生产队。二伯在生产队的猪场喂猪,兼顾杀猪的活儿。宰猪前,几个社员先把猪的四蹄捆了,按躺在柴木桌上,头颈要探出桌面,悬着空,猪头下方放一只洋铁筲,接血用。三百来斤的大肥猪,拱着长嘴,瞪着眼睛,哼叫不止,拼命释放生命中突如其来的恐惧。
二伯握一把刃长七寸的尖刀,这手藏在身后,另一只手在猪脑门儿上来回摩挲。 *** 硬,根根挺立。他一边轻轻抚摸一边高声唱念,像是在完成一道发自心底的告慰仪式:
啃窝头、就咸菜,俺杀你来实无奈。
千万别把俺来怪,早晚都是桌上菜……
这一唱念,肥猪竟然停止了哼叫,一动不动地梗着脖子听,它耳朵竖立,眼睛乜斜,好像听懂了,又好像在琢磨那话的意思。但这安静只是须臾,片刻之后,它似乎全明白了,便开始大声嚎叫起来,疯狂地踢踹挣扎。
围观社员多了起来,以“二师兄”为中心,姿态各异地围站着,他们说笑着、讨论着肥猪能放出多少血,割下多少斤肉……这些肚子里缺少油水的人,期盼着用它的肥膘来荤一荤家里的铁锅。
二伯俯 *** ,轻轻摸着猪的脑门,嘴唇近得快要贴到猪耳朵上了,才含糊嗫嚅出一句无奈的话:晌午我也没少喂你豆渣,早死早托生,俺的好乖乖,上路吧!瞬间,他手中的尖刀便欻的一下直捅在了猪脖子的下方,温热腥鲜的猪血汩汩涌出,砸得洋铁筲的薄底梆梆作响。
二伯开始忙乎了,捅皮、吹气、烫水、刮毛。约莫半个多小时,大猪就被褪得白白净净,鲜亮喜人,契合了社员们的视觉要求。
挂上肉杠剖腹摘肠之前,头 *** 事,需先斩下猪头。二伯双手握一把锃亮的铜头 *** ,手臂抡成半月圆,朝着猪的后脖颈“ *** ”猛然劈砍两下,揪住肥厚的扇耳用力一提,一个敦敦实实大猪头便离开了猪身,旁边撺忙儿的社员赶快接过来,欢喜地看上两眼,便掷在事前准备好的铜旋子里。二伯又换了一柄一拃来长的短刃刀,紧挨着脖颈处,刀尖极为娴熟地转了个圈儿,就像用细篾儿划了个印道儿,二指来宽带着鲜红血迹的一条子颈肉,便被他手指钩挑起来。他扯了一嗓子——
馋嘴娃娃,吃不够,血脖二刀咯吱肉!
二伯勾着“血脖儿”手指,只那么一晃,就把肉甩到了我母亲臂弯??着的篮子里。
血脖二刀,是猪身上最不好的部位。在屠宰时,它沾上了鲜红腥臭的猪血,清洗不掉。而且猪脖这个部位,是淋巴 *** 区域,吃的时候,肉在嘴里来回翻腾也嚼不烂,还会有咯吱吱的响声。老人们说,“血脖儿”肉,不能吃,那些硬硬的 *** 子里有毒。
在那贫穷的岁月,哪里还有人不能吃的东西?血脖二刀生产队不要,被视为下脚料由二伯自行处理。因此很多社员豢养馋虫的 *** ,都寄托在二伯手上的分寸。
母亲仁慈,她把猪肉递还给二伯,再切成多个小块,均分给了另外几个家里有小孩儿的人。
食材虽然难得,但是做法也尤为关键。我从小体弱,母亲为了给皮包骨的儿子多些营养,她万分小心地对这块猪肉进行烹饪前的深度处理。这是一个简单而烦琐的程序。
血脖儿含有大量淋巴结、脂肪瘤和甲状腺。淋巴结里会积存病菌和 *** ,短时间加热也不易将其杀灭,所以食用后很容易感染疾病。母亲并不知晓这些,她只知道心疼他的儿子,肉里面这些疙疙瘩瘩,会对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母亲等到下了工,把血脖肉切成薄薄的肉片。这活儿必须在夜晚 *** 作,因为晚上家里才会开电灯。母亲取一片肉,贴在一块巴掌大的玻璃上。她拿着玻璃片的边缘,努力靠近灯泡,晕黄的灯光从玻璃片后面射来,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肉片里的肉粒子,然后另外一只手捏一把锥子,把那些肉粒子逐个挑出。拳头大小的那么一块肉,她要足足挑上两个夜晚。
烹饪血脖二刀,母亲常是佐以水田边的野芹。野芹气味清香,与猪肉搭配,互相激发,色香味均可提升,堪为我心中的之一美味。但是,于我而言,最后剩在盘碗里的,仍是那惹人眼睛的嫩绿芹叶。
母亲厨艺过人。在我记忆里,她能把那些生长在荒野沟塘粗糙、低端的食材,变换花样,烹制出我喜欢的味道。比如荠菜咸粥、白薯叶粥、咸蛋黄焗倭瓜、炕洞焐家雀、煎毛蛋、铛包鱼儿……
我说母亲这些拿手菜、“横”菜,都和我嘴馋有关系。
她却反驳道:是穷苦的日子把人逼出来的。现在的“好日子”天天像过年,再馋的人,也不愿吃那“血脖二刀”!
《 *** 》( 2023年01月20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 *** 》
夜雨丨施崇伟:老家年味悠悠长老家年味悠悠长
施崇伟
爆竹长一声短一声的敲击窗棂,腊香在炊烟中氤氲而起,把我的思绪牵引,引向西边老家的方向。故乡的年味,阵阵袭来……
老家隔得不远,在百公里外的乡下。那里古树苍苍、溪流潺潺,竹园撩起清风,老街流淌乡愁。更喜欢年关时节,杀年猪,炸酥肉,走亲戚,祭祖先,赶庙会,玩龙灯……那连绵不断的年节味道,像注入我身体的玉米白面,经年累月地滋养着我的灵魂。
进入腊月,年味弥漫开来。腌青菜和腌猪肉,是两桩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来年全家人幸福生活的事情。母亲开始忙乎起来。当薄纱般的轻雾散去,山丘散漫着温暖而慈祥的阳光,田野里,生长了几个月的青菜又肥又嫩。母亲把青菜从地里砍回来,清理掉黄叶,清洗干净之后再一棵一棵挂在院坝里,让太阳慢条斯里晒上几天。等青菜从一掐就会出水的鲜嫩,变得有些蔫的时候,母亲把它们搬到屋檐下的那只大瓦缸前。她熟练地把青菜捏在手里,一棵接一棵地抹上盐,再细心地叠放进瓦缸。之后,还要在瓦缸上面仔细地盖上塑料薄膜和蓑衣。十来天后,从密封得严实的瓦缸里,挤出一丝丝酸酸的滋味。母亲把蓑衣和塑料薄膜拿开,里面的青菜已经腌熟,紧缩成小小的一团。足够一年食用的腌青菜到此算是大功告成。
紧随腌青菜而来的是更加隆重的杀年猪。那头养了一年的肥猪被技能娴熟的 *** 庖丁解牛般分割成三五斤不等的条状。接着,母亲把它们搬到屋子里的另一只瓦缸前。一把把的盐抹在还滴着血水的猪肉,再交叉放进瓦缸里。四五天左右,她把猪肉从瓦缸里取出来,一块块挂在灶台前的房梁上,让一日三餐的人间烟火不停地熏。要不了多久,猪肉变成了黄褐色。腊肉,就是这样腌熏出来的。
在乡下,一个殷实家庭的标志,就是一大缸的腌菜和一大缸的腊肉。因为父母的勤劳,我家年年都有。
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来了——除夕,乡亲们更习惯叫过年。大清早,各家各户就忙碌起来。重头戏是煮长菜,把腌熏的猪脚、猪头请出来,放在火上烧,放进水里泡,刮去烧焦的毛皮,露出 *** 的 *** 。一口大锅早已烧得沸腾,当猪头、猪脚炖得满园飘香的时候,一大筐白菜、萝卜也跳进油浸的热锅欢腾起来。大人们捞出一块骨头,打发垂涎在锅边的孩子,一边说:“长菜一直要吃到元宵节的,寓意幸福生活久长久远。所以,省着点。”
一块带肉的骨头哄了馋嘴,娃娃们又追着上过学的大孩子去贴春联、年画了。贴春联得讲 *** ,大孩子读过书,能识文断字,才不闹出上联下联反贴的笑话。写春联的是在县城上中学的更大的孩子。我在老家那些年,就经历了从看贴春联,到贴春联,再到写春联的成长过程。最神气是写春联那会儿,吆喝着比我小点的孩子,给我倒墨水、掀红纸,写好后,再规规矩矩摆在院子里,像自己办的书法展。其实,我的字至今都写得歪歪斜斜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前大道通车马,屋后青山润 ***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些对联,写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红的对联一贴,就有了除旧迎新的气象。
年夜饭当然是最隆重的大典。盼上一年,才有这一餐的丰盛。堂屋正中的 *** 桌,一道道大菜八卦图似摆上了:回锅肉、夹沙肉、红烧肉,比着香味;炒耳块、红番茄、素青菜,赛着色调……年长的爷爷奶奶坐在上首,爸爸和叔叔面前摆着大碗高梁酒,在灶房作大厨的母亲一到位,孩子们就争抢起来了。热热闹闹一大家,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聊着笑着。今年的收成,来年的打算,孩子上学的事情,叔叔找婶婶的话题,都是下酒佐餐的“美食”。
如今,日子变了,吃得天天都像过年一样好。但回家过年,仍是每一年的期盼。过年,我还得回一趟老家,补上家乡的年味。老家的山山水水、乡情乡音,是我心中永恒不变的温暖。
编辑:罗雨欣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中秋有惊喜,今年的月亮格外不一样今宵明月最圆光
睦睦全家聚一堂
馋嘴娃娃吃月饼
爸爸对月想文章
——《蜀中风俗图咏》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之一。
赏月、吃月饼、放孔明灯、全家团聚,全国各地习俗多种多样。
关于中秋月亮也还有许多美妙的故事,今年中秋节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圆月”。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这一轮“圆月” 与众不同,想要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哎哎哎,不要着急,它将在第五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与大家见面!
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一睹它的芳容了?
那么我们在天津直博会不见不散哦~
2019年10月10-13日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航直升机产业基地2号馆B101
期待与您相遇~
邻居阿姨的妈妈患有老年痴呆症,她们村里正在 *** ,将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在网上查了下,这病是这么说的: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 *** 发展的神经 *** 退行 *** 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 *** 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老奶奶在帮女儿看柿饼。
老奶奶今年 *** 岁了,快90岁了,在村里都算长寿那辈了。小脚是过去家里绑的,现在还习惯穿那种尖尖鞋。
翻起来看柿饼,底下有柄。记得陕西兴平的柿饼是挂起来晒的。而陕西咸阳彬县长武县一带,是放在席子上晒的。
因地制宜,这是阿姨用苹果枝编的席子,每年用来晒柿饼。
这个是从树上下来就摔烂的,晒晒就吃了。
这半截席子是用笤帚秆编的。
统一起来看,还挺美。
老奶奶一直在嘴里念叨,这柿饼要给我儿我孙子过年吃,过年吃,过年吃。一个 *** 能说半天话。可是,谁也不知老奶奶心里记的她儿她孙子是哪年的样了。因为儿和孙子站在她面前,她都认不出来。唉,怎么会有这种病,这是村里这些年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这可恼了她女儿,明明在我家,还记着你儿子你孙子,连我这个女儿一句都没说。
看着老奶奶看柿饼,想起我妈妈每年也会给我晒柿饼。我们喜欢吃还未晒成的半成品,妈妈喜欢晒的特干,咬不动的那种,说易放,不易坏。
今年,妈妈没有晒,因为家里的柿子树因为霜冻,没有结果。妈妈终于可以休息一年了。可怜 *** ,处处都为子女想。
山海情中的水花,婚姻是个买卖,丈夫成了废人,可她却越过越幸福《山海情》这部不掺一点水的好剧就要落下帷幕了,节奏快、剧情好、演技到位、满满的都是感动,人们对于这部短小精干的电视剧给了无数个的好评,真的,好久没有那么过瘾地去追一部电视剧了,整部剧里没有一个可以被吐槽的点,通篇看下来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坏人,满满的都是情怀、都是感动、都是正能量。
要说这部剧里的好人真是太多了,正能量满满的林教授与白校长,他们真的是给当下的专家教授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什么是好?什么又是不好?人民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一个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把人们的权益摆在之一位的,那就是好的官员好的人民公仆。
这部剧还有两集就要大结局了,真是满心的不舍得,像个馋嘴的娃娃,对于好的东西真不忍心放下,没有办法精品太少了,还是且行且珍惜吧,现在回过头来评说一下剧中的主要人物,好像都有了不错的结局,不过,纵观下全剧,可能让人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那个苦命的女子水花了。
为了金钱, *** 棒打了 ***
其实,年少的水花与得福是有过一段感情的,可是,得福为了那个家,他最后还是放下了水花,而没有了感情依托的水花,只想一个人远走天涯,可善良又孝敬的她,终还是不忍心让她的老 *** 遭人打骂,她为了亲情也为了那个失去的爱情,她嫁给了一个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男人永富。
她爱永富吗?我想是不爱的,当她在得福那里失去了爱情后,她就心死了,既然没有了爱情,那么婚姻对于她来说,就是找一个男人嫁了,这个男人是永富也好是阿三、阿四也罢都没有什么关系,爱情已死剩下的只有生活。
生活就是二个人的搭伙过日子,苦也好乐也罢,只要活着就好了,不过还好永富对她不错,她在身心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生活对于她来说已经知足了,所以,她一直都是开心的,为什么她在那么苦的条件下还能那么开心呢?那是因为,她对于生活的预期很低,只要能好好活着就好了,其他什么的得到了就应该满足了,所以,在她的脸 *** 基本上看不到愁苦的表情,可能,她唯一的一次落泪,就是她与得福的分别吧,那一次,是她与爱情的彻底诀别。
为了生活,她永不放弃
在这部剧里,之一次落泪的就是看着水花拉着永富与孩子走了七天七夜的那人镜头,在那一千多里的路上,她一个女人面对着风沙,面对着未知的明天,面对着无边无际的 *** 滩,她却一直在笑着,一直在走着,一直在唱着,是什么样的 *** 支撑着她前进呢?
是活着,一定要好好活着,这时的水花其实目标很明确了,以后的生活就是要好好地活着,此时的她已经有了孩子,而她与永富也过了初婚时的尴尬期,只是,此时的永富却成了一个废人,他的身子不中用了,可是,他是孩子的 *** ,他们是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有 *** 、母亲还有孩子,他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此时,水花的目标已经很清晰了,那就是以后她要担起这个家的重担。
对于永富,她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爱情,但是,现在她要对这个家负责,要对孩子负责,生活谁也指望不上,只有靠自己,在生活里累一些苦一些都不怕,就怕没有了向上的勇气,为了新的生活,她来了,她带着一家老小来了,在新的天地里,她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生活一定不会太差,所以,她一路笑着、一路走着、一路前进着。
很多人不能理解,说生活对于她来说是这么的不公平,可她为什么不抱怨呢?她为什么不放弃永富吗?以她的条件,她再找一个也不是不可能,可是她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她善良、她知恩图报、她还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她与永富虽没有什么爱情,但是永富对她好她是知道的,永富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才去打井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能抛弃永富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为了孩子她也不能让孩子活在人情寡凉的环境下,所以,她不能放弃永富,他们三个人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在这个家里只要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幸福的可能。
幸福的人,能看清楚生活,更能看清楚自己
水花一个苦命却幸福的女人,生活给了她了一个又一个的痛苦,可她却把这些痛苦变成了欢笑的甜蜜,在她的脸上永远都带着淡淡的笑意,这种微笑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回应, *** 佛的生活,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食,快乐无比,在中国,你看颜回,箪食瓢饮,不亦悦乎!他那个乐从哪里来?觉悟。
生活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活得痛苦,那只是因为,他老是盯着自己的不快,而又去想着别人的快乐,这样的人他总是在不平衡中越来越痛苦,天气晴好时他很烦,天气阴沉时他更烦,有了房子他要还钱痛苦,没有房子他更痛苦,他吃不了苦又受不了罪,老想着天上能掉下一个馅饼来,每天不是怨天尤人就是唉声叹气,这样的人不光他觉得苦,在他身边的人都会被他带着而受苦。
其实幸福是什么呢?幸福不是能住上多大的房子,能开上多好的车子,能穿上多体面的衣衫,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的笑脸,水花为什么能越过越幸福,就是她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一种永不服输的生活态度,最后,她不光种好了蘑菇还开了商店,不仅与永富家庭和睦,还当上了村干部,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全是满满的正能量,所以,她才会越来越幸福,而且,幸福从来都不是别人能给予的,幸福永远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九月艳阳高照,
大地丰收尽显!
高粱涨红了脸庞,
谷穗笑弯了细腰!
沉甸甸的稻子金光闪闪,
硕大的白菜叶子油光发亮!

蚂蚱蹦蹦跳跳欢愉雀跃,
忙坏了小孩子捉个不停!
大人们忙碌着收割,
银色的镰头闪着光芒,
拖拉机突突的响,
满载着丰收的希望!
牧牛的老伯最是美食家,
趁着牛儿悠闲的吃草,
一堆干草已经拢好!
催烟袅袅升起,
干草噼噼 *** 像在燃放喜庆的鞭炮!
土豆玉米被烤的金黄,
*** 的香味弥漫四方,
馋嘴的娃娃忘了回家,
小嘴粘着糊渣,
小肚吃得滚圆,
应着妈 *** 呼唤,
不忘拿上新打的乌min,
踏着暮色的夕阳,
寻找各自的回家的小路!
小路虽小,只够一人行走,
路边的野草也会错综交替,
夜色阑珊星光出现,
但都不影响娃娃回家的脚步,
因为路的尽头有妈 *** 等待!